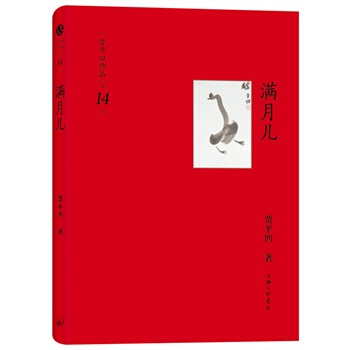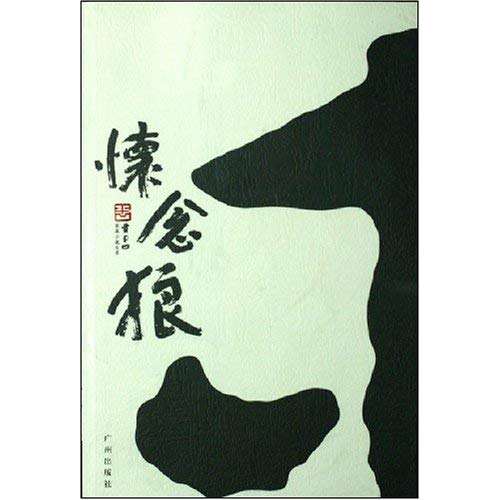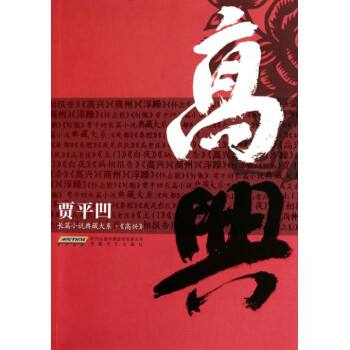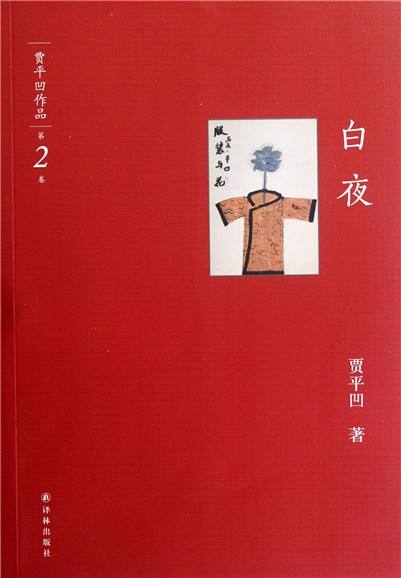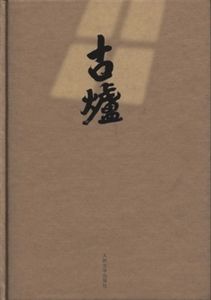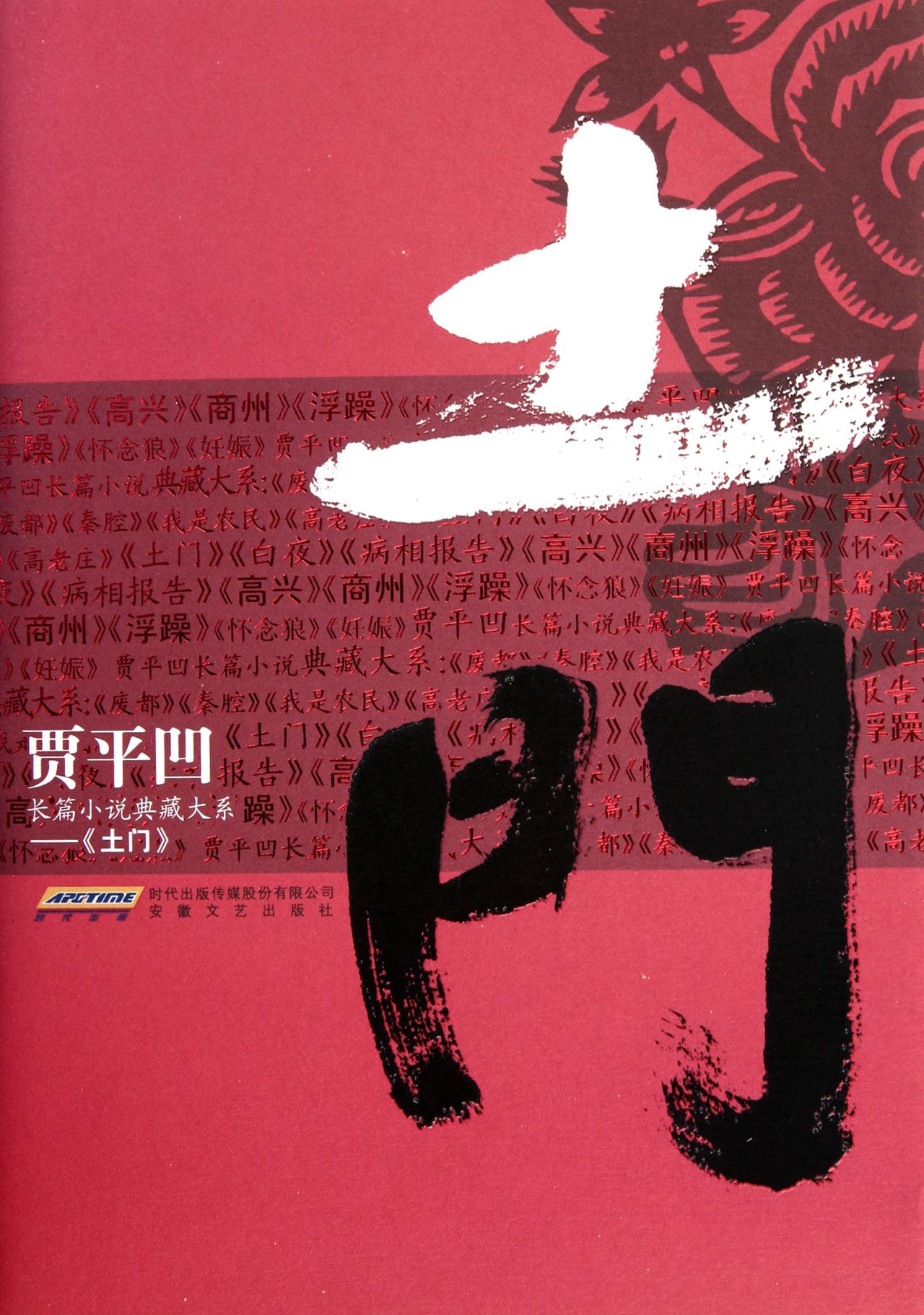张载说“有象斯有对”。有写书的,就有读书的。我天生愚笨,不会写书。但是,我却是天才读者。 一个人是作者还是读者,都是命定的,由不了自己。作为读者的我总是想,先有读者,才有作者。不是作者满足读者,而是读者催生作者。这与市场需求决定企业生产是一样的道理。不然,作者写的再好,适销不对路,还不是白写?60岁的我,有50年的读龄。每当想起,是我催生了贾平凹,便不由自主地飘进土谷祠中去了。50年阅读,有40年像盗贼盯着一家打劫那样,盯着一个作家一路读下来。到如今,作者读者,双双变成白头宫女,不禁感慨系之。 读者催生作者,作者引领读者的风景,只发生在我与贾平凹先生之间。 写书,是贾先生的使命;读书,是我的宿命。我们命运相通,如影随身,不亦快哉!不亦乐乎! 1978年10月,我考上凤翔师范。语文老师宁克俭给学生讲《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》,说的天花乱坠,五彩缤纷。可是,私下却对我说:“(文章主题)太沉重,(感情)太扭曲,(话语)太矫情,硬写。远不如贾平凹好,贾平凹不硬写,有鬼才灵气,作品如空谷足音。”宁老师还提到莫声、王缵叔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贾平凹并知道他的文字好,是“空谷足音”。40多年了,莫声推开《窗口》之后,自己消失了。王缵叔先生成了茶博士。只有贾平凹先生,任我跟踪打劫。 宁老师讲课后,我就想读贾平凹。这时候,学校为纪念柳青去世一周年而举办“《创业史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”的报告。报告人是陈宗田老师,报告结束语是“而今雪翁大行后,问谁此后做鹗公”。他解释说:“《创业史》计划写3卷,柳青先生只写了一卷,放眼陕西文坛,只有一个青年作家贾平凹能够续写。”《创业史》当时被誉为“诗史般的作品”,中国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。陈老师讲,有个读者把《创业史》读了27遍。《创业史》中包涵中国农村、中国人民,通过人民公社这个金桥,走向共产主义的密码。要是续写,非贾平凹莫属。 听了陈宗田老师报告,我放下对贾平凹的寻找,赶紧读《创业史》。初中语文课文从《创业史》节选的《梁生宝买稻种》,让人感觉不到是小说,而是通讯报道。我当时被感动得五体投地。这次我读《创业史》,看你能好到什么程度。 我是农民。我比谁都清楚地知道农民。我以朝圣之心读《创业史》。可是,阅读越恶心,一点点觉不出它好在哪里。情节不是“虚构”而是“伪作”。失望之余,我就去读贾平凹,看“鬼才”如何续写“伪书”? 说来也巧,在一本大32开的杂志上,我读到贾平凹新作《阿娇出浴》,旁边还配有插图。哇噻,这是啥嘛!贾平凹,原来是“色情”写手。 什么鬼才?什么空谷足音?色情,《创业史》《苦菜花》都有,那是腌臜地主婆子的。你贾平凹竟然写色情?我的思想很“马克思”。对贾平凹,也失望了。 1980年7月,我师范毕业。离开母校前用学校补发的剩余助学金买了许多书。例如《醒来吧 弟弟》《伤痕》《生活的路》《于无声处》《第二次握手》,偏偏不买贾平凹,嫌他“黄”,嫌他“色”。 1980年秋冬,收音机中有广播剧联展。《满月儿》的作者偏偏就是贾平凹。哇噻,太好了!满儿月儿姐妹俩的笑声恰如空谷足音,在群山万壑中飘荡,在蓝天白云间回响。咯、咯、咯,嘻、嘻、嘻,呵、呵、呵,黄澄澄的菜籽花,绿油油的小麦田,翠生生的茶树坡,除了大娘她二姨,还有那狗那公鸡。没有院墙的屋宇中的两个姑娘,姐姐满儿,妹妹月儿,快乐仙子,撒花天女,是我梦中的情人。那年我20啷当岁,一心只想,满儿月儿,娶一个做媳妇,这辈子就没白活。娶进门,我不叫她搞“科学实验”,我只惹她笑,对我一个人笑!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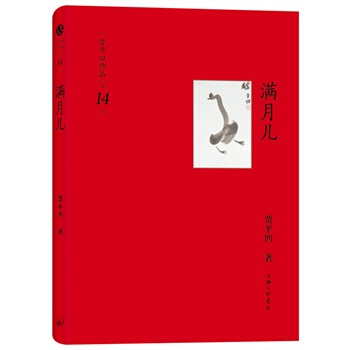 我爱上了这姐妹俩,自然也喜欢《满月儿》之父贾平凹。《阿娇出浴》之印象,一扫而空。 从此,“读贾”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主轴。贾先生以散文见长,又以散文笔触写小说,以鬼才眼光看世界,以调侃心态对人生。清新明快的语言,浓郁芳馥的生活,常识莫测的神秘,幽深遥远的寄寓。春秋笔法,皮里阳秋,反讽手段,入木三分。进入贾府,如行山阴道上,移步换景,美不胜收。 贾先生正在全力打造他的文学贾府:商州。屠格涅夫有草原,肖洛霍夫有顿河;沈从文先生有边城,老舍先生有京华。贾先生,是生命作家,是贾府造物主。贾先生,是使命作家,他生命的底色是海天之蓝,是生命之绿,是赤子之红。他的作品中“黄”与“色”,正如神灵与天使的男根,咋能与流氓混为一谈? 读之既久,知之愈深。贾先生有“三突出”的痕迹,有“主题先行”的轨辙,有“硬写”的挣扎。党八股,草蛇灰线,若隐若存。例如“硬写”,这是违心的“革命写法”,只有“顺写”,才是真心的“生命写法”。这是宁克俭先生在讲老舍《文学概论》时说的。写作就是挤手背上的脓,如果挤出血,那就是“硬写”。以此观之,贾先生也未脱俗。世人希望由他续写《创业史》,并非空穴来风。我对贾先生是喜欢的,但是,对他“硬写”,是不喜欢的。 1987年9~10月间,我回母校陕西教育学院学习。见到胡耀邦同志昔日秘书、中文系教授沙作洪先生。他在校门口大发雷霆之怒,为老首长胡耀邦下台打抱不平。沙先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。他掷地有声:“这样浮躁,这样轻率(指胡耀邦去冬被迫辞职),党何以堪?国何以堪?民何以堪?”“贾平凹写了个《浮躁》,你们看看,好好看看啊”“小说才是历史。史书都是伪造。”先生狮吼雷音,几次蹦出贾平凹仨字。  沙教授学术与政治威望都高。听完他的演讲,我连夜通读《浮躁》。 州河、白石寨、两岔镇;金狗、小水、英英;田家、巩家、雷大空。白石寨是大中国,金狗是中国人,曲折的州河,就是时代发展的进程。金狗一生坎坷,但他与小水的恋情却修成正果,小说结局大团圆。这也是“硬写”吧?我是州河上先知的鸭子。我不认同贾先生在小说中暗示的故事一定成功。 《牡丹亭》中,汤显祖不叫杜丽娘死,《红楼梦》中,曹雪芹让贾宝玉封妻荫子,作品就失败了。作品一开头,就有祂自己的生命,由着祂自由地成长。可是,贾老师怎么能“控制”作品结局,照政治需要,这样写呢。我有点失望。 对这个结局,小说中说:“上帝是不是存在,只有上帝知道。”浮躁下去,就是死亡嘛 。先生为什么不让该死的去死呢? 浮躁,是州河上的浪花。风筝没有线,轮船没有锚,人群没有身份标识,社会没有是非标准。大家摸着石头过河。 读竟全书,对改革开放,我竟然有莫名的恐惧。老子说“重为轻根,静为轻君。”浮躁尘埃落定之时,怕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吧。 我把自己的理解在同学们中一讲,大家骂我是美国佬跟屁虫,贾平凹是中国的“新思维”云云。《浮躁》获得美国文学大奖后,更有人骂贾先生是汉奸,迎合美国佬。可怜我作为读者,白白儿陪了一回杀场。 贾先生的心态是矛盾的,写作状态也是“浮躁”的。似乎先生的身后,站着一个警察。下笔不由自主,情节安排生硬机械。尽管往政治屁股上靠,可是,政治却不喜欢。作为读者,我能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。从“浮躁”视角观察中国的改革开放,贾先生是第一人。 越10年,读经济学的凯撒大帝杨小凯先生著作,《浮躁》的暗喻,与杨先生理论如出一辙:改革开放没有是非标准,没有目标定位,没有正确的理论预设,如此“浮躁”,可能是一场瞎折腾的悲剧,到头来,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。 歌德比康德深刻,托尔斯泰比普列汉诺夫深刻,曹雪芹比孔夫子一点不差,《水浒》比得上《论语》。贾平凹比思想家更有洞察力。回望贾平凹,我不能不惊诧他对“浮躁”的发现,是多么具有前瞻力。作家是历史的巫师。诚哉斯言。 从《浮躁》开始,贾先生一发而不可收。从商州迈步,先生沿山本一路走来。走出商州,跨过土门,不用带灯,循着白夜,走入废都,看看这里人们的病相报告。先生长篇,联翩而至。可是,他写的再快,也没有我读的更快。贾先生是只牛氓,历史是头老耕牛。牛氓盯在牛背上,催牠走得更快。可是,我却是提着口袋,等在地头要装粮食。作者读者,面对同样的社会,同样的瘔焦。作者总比读者积极,读者总比作者从容。  等不多久,《废都》突兀而出,里程碑式的文学作品矗立在“废都”上。 要了解明清两朝,不要读《明史》《清史》,读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;了解欧洲近代史,不用读“史家之绝唱”,读《人间喜剧》,这才是“无韵之离骚”。这也是恩格斯的观点。 斗牛场上,毕加索画的牛,吓跑了真牛;悬挂梵高的《向日葵》的房子玻璃窗下,碰死一堆蜜蜂。艺术总是高于生活,艺术比生活更真实。卓别林参加模仿卓别林大赛,海明威参加“最像海明威”比赛,都只能得第三名。演员比主角本人,更像本人。这就是艺术与艺术的魅力。 艺术比生活更真实。艺术 ,只有艺术才能反映生活的本真。只有艺术家才可以和上帝的心灵契合,和上帝对话。贾平凹先生,就是这样的文学巨匠。 《废都》就是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《人间喜剧》,就是《向日葵》《斗牛》。《废都》中的“废都”,比生活中的废都,更接近生活本身与本真,更凸现生活的荒诞、荒唐、荒谬。 《废都》是《浮躁》的后篇:又是一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。废球,废国,废都,废人,非心。人都成了“身上没长毛的两足走虫”,除了饮食男女,无所事事。白天等待黑夜,活着等待死亡,男人等待女人,吃饱等待性交。回忆初读《阿娇出浴》时的不愉快,我简直就是白痴。 《十日谈》不黄,不足以表达伪教士的虚伪和人性的丑陋,何以吹响启蒙的号角。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没有野性的翻滚,就没有文明的呼唤。中国是个废都,啊,5000年的努力,全都废了。 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中国没有道,人都成了性交机器。“废都”翻过来读,不就是“都废”么?苦哉兰陵笑笑生,以大慈大悲菩萨心肠写成《金瓶梅》,谁解其中味呢?没有钟子期,俞伯牙不甩琴,得乎?不要怨中国没有大作家,要怨中国没有好读者。几百年没有读懂《金瓶梅》,几十年怎么读懂《废都》?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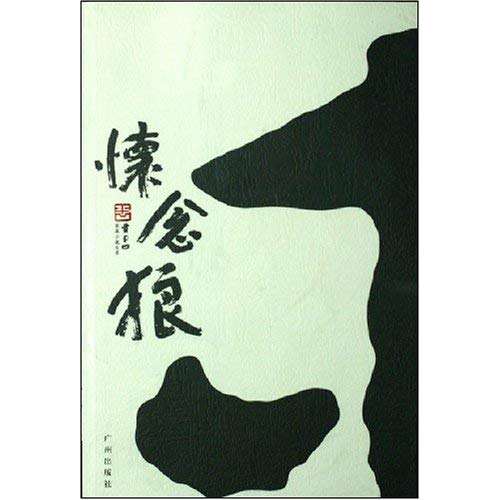 贾平凹先生是孤独的独行侠。好在有我等读者在! 《怀念狼》出来了。尼采说,古希腊文明是酒神与日神的“二人转”,也就是“野性”与“理性”的“交响曲”。中华文明依然。狼为什么值得“怀念”?因为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法西斯”,也就是一匹狼。狼性是人性的催生婆。没有狼性的人是不完整的人,没有狼的自然界,是有缺陷的土地。这样说来,《怀念狼》又是《废都》的姊妹篇。 狼性就是人的野性或酒神精神。人如果没有狼性,神性就失去了依托。过度的理性,是人类的自残。怀念狼,就是呼呼完整的人性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,人性的一半是狼性。为什么不能“怀念狼”呢?惜乎“茅奖”评委,读不到这个份儿上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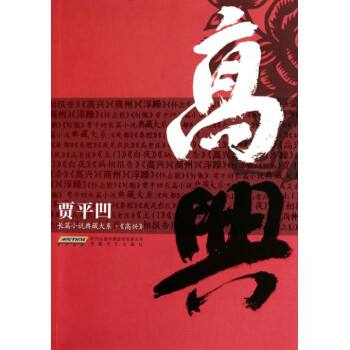 《高兴》来了,他很“痛苦”。高兴是进入现代化、城市化、世界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化身。“高兴”向城市、世界、历史发问:谁是城市化、世界化、现代化的埋单者?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建它的人只能一仰再仰看看它,用伏仰交替治疗颈椎病。姐姐只有终生卖淫,才能供养警察去抓杀害弟弟的凶手,才能维持治安,甚至去抓嫖客。抓嫖客的多与少,就看女人卖淫的多与少。可是,来嫖风的往往不是需要女人的人。光棍汉只能到供着妓女神的锁骨菩萨那里烧柱高香,过过生理瘾。真正的妓女都叫阳痿早泄的男人浪费了。公安是妓女和嫖客的催生婆。这就是《高兴》的主题。你高兴得起来吗? 衔着眼泪,读完《高兴》,一声《秦腔》,空谷足音:我来了! 周秦汉唐,都当“中国”讲。秦腔,不是陕西地方戏“秦腔”,而是“中国之声”。作品采取陀思妥耶夫斯基“双调”或“复调”写法,明里写地方戏秦腔没有观众,只能给人送葬,唱挽歌;暗中写“中国传统文化”“中华正统文明”,也就是农业文明后继无人。一次秦腔演出结束,台下还有一个“忠实”观众,演员好不高兴啊。可是,人家不是观众,人家精神有问题,稀里糊涂来到台下,把钱丢了,人家寻钱呢。“引生”就是“断生”,小说一开始,主人公就割自己的男根嘛。风花雪月本指男欢女爱,可是,“夏风”娶“白雪”,爱得上吗?孩子没有肛门,“无后”啊。夏天仁,夏天义,夏天礼,夏天智,偏偏没有“夏天信”。诚者,信也。不诚无物,失信就是失诚。夏是中国,夏是传统文化啊。夏家无后,其谁知之? 作者不是为棣花镇树碑立传,而是“中华涅槃,立此存照。”作者被传统文化所化,当传统文化死亡之际,用陈寅恪先生话说,贾先生会比谁都更加痛苦。所以,贾先生有王国维先生那样自杀以殉文化的悲壮情怀。可是,贾先生为何不死?这个答案,只有司马迁能够替贾先生回答:“活着尚且不怕,还怕死吗?”人生为一大事而来,这就是“使命感”。贾先生就是为我农业文明,传统文化“立此存照”而来!  文学博士李建军先生,捡出《秦腔》中的主人公引生语录和引生的龌龊行为,腌臜贾先生“恶心”,否定《秦腔》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蕴。作为读者,我要问:能用薛蟠的诗句与不雅动作否定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吗?薛蟠越无良、无能、无德,行为越恶心、龌龊、猥琐,《红楼梦》的美学价值越大,曹雪芹的文学功力越高。这是作品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,由不得作者的。丑角不丑,以丑彰美。反者道之动。艺术辩证法,文学博士竟然不懂。这才是中国文学的悲哀。 《白夜》《土门》《极花》《山本》《古炉》《高老庄》《带灯》。。。贾先生的创作,好比天女散花,七彩祥云。他突破他自己,走出商州,来到废都;走向中国,走向世界。近50年的连续高产,只有莎士比亚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蔡东藩、张恨水、金庸等少数超一流作家可以比肩。贾先生写的越多,我读的越快。他累不死我,我却要催逼他。他是栽种人参果的果农,纵然不要500年开花500年结果,可是,我是猪刚毅,眼巴巴的看着果子快快成熟,大快朵颐。 “庾信文章老更成,贾生才调更无伦。”贾生活成了庾信,文章能不“更成”乎。贾先生不仅创作时间长,作品数量多,而且越到老来,越是优生优育。先生旧作与今天的作品比较,几乎都是残疾人。从前党八股、三突出、政治先行,还有别人发现不了的“乡愿情结”,如今通通遁形,略无踪影。先生笔触,逍遥无碍,自由自在。咳唾成珠,撒豆成兵。每次出手,皆能扛鼎。先生是中国特定时代的秘史作者,“起居注”作者。贾平凹,正在为一个时代,立此存照。 那些假道学、真伪善的人,抓住强奸犯人的床头,放有《废都》而否定贾先生。请问:强奸犯还吃过饭,穿着衣,难道要把做饭制衣的人都否定吗?强奸的根子,是他有男根,难道要把造物主否定吗? 贾先生就是《皇帝的新装》中的那个小男孩。说出真相,不需要技巧,也没有什么原则。假道学、真伪善的家伙就是皇帝的新装中文臣武将,有什么资格“批评”贾先生呢? 小说是民族秘史。有人说,这个世界只配上帝与诗人活着。孟子说,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贾先生就是这样的赤子。上帝创造世界,贾先生创造自己。他以史诗,为时代立此存照,为这个民族立此存照,为这个文明立此存照。仁者无敌,智者不惑,勇者不惧。在贾先生这里,浓缩成一句话:“童言无忌”。贾先生的所有作品,都是“童言无忌”,而且越到老来,越是“返璞归真”“返老还童”。质朴、质拙、质感,厚实、厚重、厚道。先生的字,是了解先生文学的一面镜子,一把尺子,一个视角。这就是艺术的“通感”。 这几年,贾先生客串书法,而且入了中国书协。朱以撒先生不乐意了。朱先生如同李建军博士批评《秦腔》一样,吼贾先生的书法。余期期以为不可。如果以朱先生的标准为标准衡评书法,则天下没有书法。就好比以中国美女为标准衡评美女,天下就没有美女一样的道理。书法是“美”,美是难的。道可道,非常道。说得出口的标准不是标准。贾先生的书法,就是童体字,原生态。回过头说贾先生的小说,也是这样。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慈祥本真“原生态”。该怎么写,就怎么写;能怎么写,就怎么写。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什么“三突出”“主题先行”“政治标准第一”“正能量”云云者,对贾先生只是“风过耳”而已矣。而先生早期作品,这些“硬伤”,俯拾皆是。这就是“返璞归真”“复归于婴儿”。傅青主论书,唯贾先生得其个中三味。 贾先生有别才、通才,他是天才、鬼才。可是,他在人格上,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,有一颗不泯的童心。没有做作,没有伪善,没有装腔作势。他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得不止。越到老来,越是童言无忌,越是质朴率真。 什么高鹗续红楼?高鹗可以续红楼,而贾先生作为“生命作家”“使命作家”,与“陕西文学教父”之称的“革命作家”“政治作家”,也就是柳青先生,在文学之路上,走的是不同的路径。好比国画与油画之别,如何去续?怕是貂尾续狗吧? 《秦腔》的历史厚重感,神圣忧思,终极关怀,也远非《创业史》之政治使命感,宣传教育感,不可以同日而语、相提并论矣。我的老师所谓的贾先生之灵气与鬼才,更不是任何一个“硬写主义”者的苦行僧可以望其项背的。龙行一步,人走百年。其此之谓乎? 贾先生的文学生命,与贾先生的书法,互为注脚,彼此呼应,相得益彰: 原生态,赤子心; 形象美,抽象意。 这12个字,就是进入贾平凹文学殿堂的“芝麻开门”。40年步踵相接,功不唐捐。做为家门“最不合格的犹大”读者,我得之矣。 贾先生的使命是写书,而我的宿命是读书。我死读书,也可能读书死,但是,我却不曾一朝一夕读死书。我认准一家去打劫。这家店只卖鲜货现货。作为资深读者,我有值得炫耀的资本。贾老师写了近50来年,我读了整整40多年。他引导我,我催促他。童心,只有童心,是我们之间的连心锁。 想当年,先生与我一并20出头,同学少年都不贱。他的新书还没有付梓,我把旧作已经压到枕下,坐在树下等着他的苹果落地,像一只饿狼等待鲜肉一样,瞪着绿茵茵的眼睛。到如今,我陪先生,双双成立白头宫女。先生“尚能饭”,我发“少年狂”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我愿意跟着他,陪着他,催着他,一直走下去。 鲁迅先生把自己比做挤出奶与血的牛,我瓜人有瓜福,有这么个精神奶牛滋养,这一生赚大了。翻过来,贾先生有我这么个读者催着写,逼着写,他也没有吃亏嘛。 巴金老人说,止境无技巧。贾先生不听别人的教导,也没有谁敢给先生指引方向,用先生朋友的朋友陈忠实先生话说,他们这些敢于指导作家创作的人“懂个锤子”。在艺术的天地,我们的贾老师,鱼翔浅底,鹰击长空。正在自由飞翔。 20多年前,贾先生推着坐轮椅的巴金老人游西湖,有人说,贾平凹推动着中国文学之车,后来巴金老人去世了,今天我要说,贾平凹先生引领着中国文学之车。 祝福近50年“作龄”的贾平凹先生继续写,也自祝有40多年“读龄”的我,继续读。先生新作还未问世,我已等候多时。 天下文章,三分写,七分读。如果有机会见到贾平凹先生,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: 好作家都是好读者“读”出来的。贾老师,你一定要感谢我,除了继续出品我喜欢的著作,就是赏我一副贾平凹书法。家有贾书不算贫。否则,我就不读了。没有我读的贾平凹,还是贾平凹吗?我“罢读”,是对你贾老师最大的惩罚。这比特狼扑关税压力大多了。 贾老师,赏我一副字吧。我欣赏你的书法没有法,原生态。一如我欣赏先生的作品一样一样的道理。
自由撰稿人杨翰章 20191115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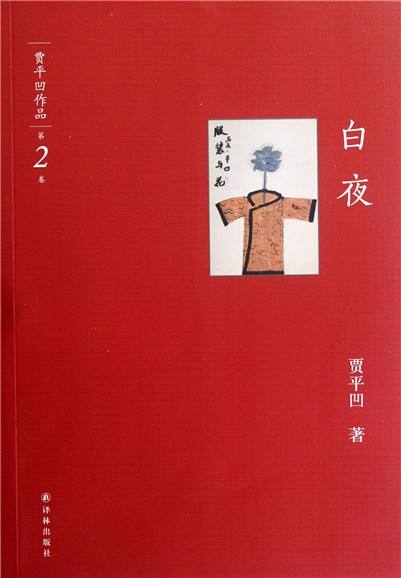 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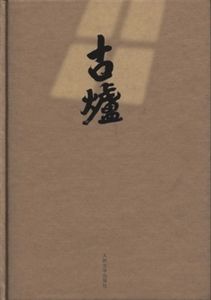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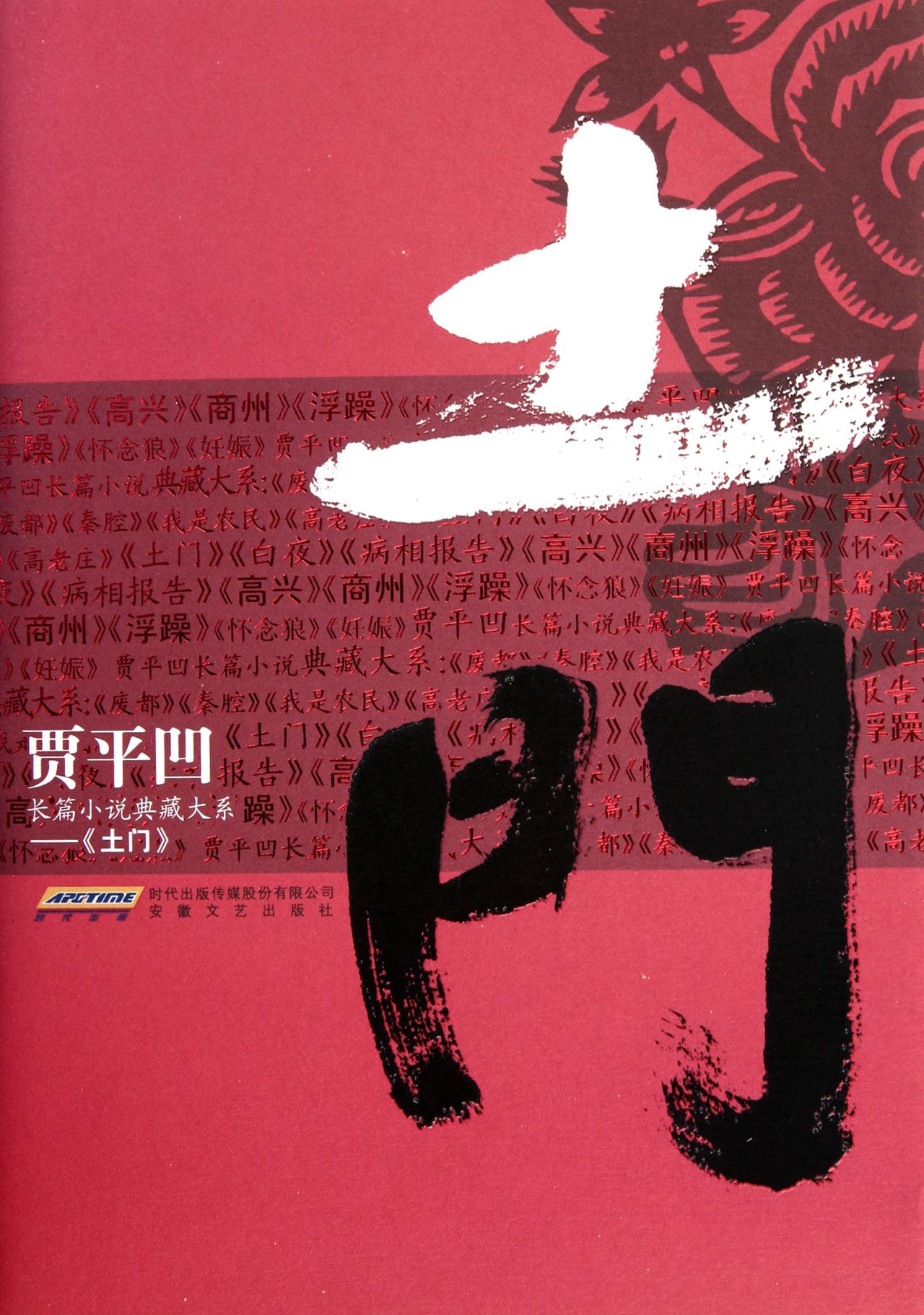
|